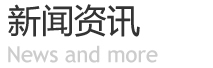風(fēng)箏的心
2017/11/2 11:36:01 From: 黃柳青
孩子是翱翔天際的風(fēng)箏,卻永遠(yuǎn)牽掛在父母手心。—— 題記
上大學(xué)是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離家遠(yuǎn)行。離家半年的我第一次嘗到了鄉(xiāng)愁。春節(jié)前,學(xué)校一放假就興沖沖地搭上最早的班車回家了。好不容易回到家,進(jìn)門的時候自己還有些扭怩,近半年沒有見了,不知道爸媽見到我會有什么反應(yīng)呢?電視劇里面父母見到遠(yuǎn)歸的游子大多是激動得手足無措、語無倫次,至少也會熱淚盈眶。爸媽會嗎?
一進(jìn)門,爸媽在客廳里看電視看得起勁,我有些不自在地喊了一聲“爸、媽”,他們兩個人齊齊扭頭看了我一眼,說:“回來了!”然后又扭頭繼續(xù)看電視了。爸媽的反應(yīng)太過于平淡了,心里難免有些失落。我徑自回房放下東西,整理房間、洗衣服、拖地等,邊做邊嘆氣:為什么同學(xué)們的父母都會把房間打掃干凈迎接他們,而我的爸媽就沒有呢?
我的爸媽絕對不是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“好”父母。
記得小時候某一年秋風(fēng)又起時,我和弟弟很羨慕鄰里孩子們放著形形色色、五彩繽紛的風(fēng)箏在大草坪上跑來跑去。弟弟望著那些高高翱翔的風(fēng)箏吵著爸媽要買一個,而爸爸只是看了看那些風(fēng)箏,指著其中一個用報(bào)紙糊的風(fēng)箏對我們說:“看到那個報(bào)紙做的風(fēng)箏沒有?”
我和弟弟點(diǎn)點(diǎn)頭。
爸爸接著說:“那個風(fēng)箏是自己扎出來的,不像別的五顏六色的風(fēng)箏,那些是買的,自己扎出來的風(fēng)箏才能放得最高,才能飛得最久。懂嗎?”
我和弟弟似懂非懂地點(diǎn)點(diǎn)頭。爸爸似乎很滿意地繼續(xù)說道:“那你們自己去扎一個風(fēng)箏吧。”那時候我們很崇拜爸爸,凡是他說的話我們都當(dāng)做圣旨,從來不會質(zhì)疑。
自那以后好長一段時間,我和弟弟每天都觀察著那些翱翔的風(fēng)箏,然后回家削一些竹片、小木棍,撕上幾頁作業(yè)本的紙張,試著自己扎一個風(fēng)箏。很快就有了成品,我們學(xué)著其他小朋友的樣子,一人拿線,一人架著風(fēng)箏起跑,但是那個風(fēng)箏卻怎么也飛不起來。
我們很苦惱,想尋求幫助。爸媽說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決,其他小朋友覺得我們鼓搗扎風(fēng)箏不如買一個省事,也幫不上我們。我們試著從材質(zhì)方面摸索,比如用日歷紙、對聯(lián)紙;支架的竹子用完了,我們就偷偷從廚房拿了幾根筷子來削。如此我們的風(fēng)箏改良好多次以后,卻依然飛不起來,我們也淡了那份心思,轉(zhuǎn)了興趣。
后來看到別人放風(fēng)箏,也不再有沖動了,偶爾會埋怨起爸爸和媽媽,為什么他們會讓我失去了放風(fēng)箏的向往?為什么不在興趣正濃的時候培養(yǎng)一下,提點(diǎn)一下?他們放風(fēng)箏的線是不是放得太松了?
長大后,隨著離家的次數(shù)越來越多,時間越來越長,鄉(xiāng)愁不再那么濃烈,家卻走進(jìn)了我的心,離家越遠(yuǎn),家離我越近。爸媽似乎也習(xí)慣了孩子在外漂泊,只是他們越來越愛打聽我們生活和工作上的瑣事,我們說話的時候他們也會認(rèn)認(rèn)真真地聽,生怕錯漏一個字。即使他們完全不理解我們的生活,也給不了什么實(shí)質(zhì)性的建議,但是他們就是想知道。他們就像那不斷轉(zhuǎn)動的線軸,寧可忙碌地轉(zhuǎn)個不停,也不愿意跟風(fēng)箏就此斷了聯(lián)系。
一次與幾個朋友春游放風(fēng)箏,看著漸漸升高的風(fēng)箏,我突然想起了小時候那只飛不起來的風(fēng)箏,想起了父母那放養(yǎng)般的教育方式,想起了他們有時候細(xì)致有時候粗糙的關(guān)懷,漸漸明白現(xiàn)實(shí)中的大多數(shù)情感都像涓涓細(xì)流,不會太過洶涌,卻堅(jiān)定又委婉地流入人心。
而那風(fēng)箏又何嘗不是遠(yuǎn)行人的心,被牢牢地牽在故鄉(xiāng)人手里?
粵ICP備05143388號